阅读量 : 11次
在没有互联网、电话、电视、收音机的世界里,印刷媒介曾经是最主要的交流工具。在影响世界深远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向民众广泛传播政治思想是争夺权力的必由之路,而印刷媒介作为唯一途径,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刷在法国大革命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印刷品不仅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记录,其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印刷促成了其所记录事件的发生,是历史上一股活跃的力量,尤其在1789年至1799年期间,当时,争夺权力就是争夺对民意的控制。《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一书通过考察印刷业,为从整体上研究法国大革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为该书《一省视角》一文,通过弗朗什-孔泰一省的视角,管窥当时的情况。澎湃新闻经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权发布。
大革命之前的三个世纪里,在弗朗什-孔泰,图书的流通无论在文化精英的圈子里,还是在贫苦的村民范围里,都在大幅度地增长。当然,出版物的种类和传播的程度会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文学需求,以及读者所居住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弗朗什-孔泰的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只有20%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随着各种印刷品的传播速度在大革命时期的加快,弗朗什-孔泰,乃至实际上整个法国都进入了识字文化的新阶段。尤其是村民们,他们接收到了大量招贴报、小册子和短文,而且还看到了报纸。
1789年之前的图书传播
弗朗什-孔泰的出版情况在几个方面都很独特。虽然这个边境地区有其独立的传统,但并未受到落后的外省心态的束缚。弗朗什-孔泰正好位于一个交叉路口上,此路口通向巴黎重要的印刷中心、里昂和瑞士,所以有着繁忙的图书流通。这个地区还承担着连接瑞士与洛林(Lorraine)、勃艮第,以及法国腹地省份的任务。在这里,除了有公开的、许可的图书商贸活动之外,还存在利用地下渠道进行的印刷品非法贩运活动。
弗朗什-孔泰的居民正好处于那些著名出版中心的出版物很容易就能到达的区域,所以购买的出版物很大一部分都出自这些出版中心。人们旅行的时候会购买图书,但更常见的还是通过书目和订购的方式来购买。因为当地的图书生产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和兴趣,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所以弗朗什-孔泰的书商——主要有25家——会向这些出版中心下订单。当地8家印刷商主要印制宗教小册子、初级读本和传统的通俗读物,偶尔也会印制一些神学书、当地或地区的历史书,或者法律和医学方面的文本,但这些还是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弗朗什-孔泰的文化精英相对来说不是很多。1789年,在大约80万的总居住人口中,有定期阅读习惯的、受过教育的公民大概只有1万,其中大约3500名教士、2000名贵族(这个群体中的教育水平也大有不同)、2000名中产阶级职业人士,主要是律师和公证员,另外还有许多医生和一些工程师及商人。分布于不同市镇的学校有15所,不到3000名学生。在如此情况下,图书市场,尤其是价格昂贵的图书市场还是受到了限制——通常也就400—700名潜在顾客。因此,像《贝桑松和弗朗什-孔泰的历史年历》(Almanach historique de Besançon et de Franche-Comté)这样一本将受过教育的公众群体设为目标读者的书,一版就印制了500本。纪尧姆神父所著的历史著作《萨兰的老爷们》(Sires de Salins)以四开本印制,一版印了700本,都是以订购的形式出售的。另外我们还得知,1777年的四开本《百科全书》也有392名订购者。《弗朗什-孔泰公告》(Les Affiches de Franche-Comté)周刊创刊于1766年,目标读者也是相同的这批公众群体,但运营十分艰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多次中断出版的情况。
虽然市场规模有限,但文化精英对于现代观念和发展趋势还是带着一种接纳的态度,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他们的图书室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的图书室往往藏书几百,甚至超过一千卷。书架上,与世代相传的古老卷册并排着的都是新近出版的著作。
精英们最初对《百科全书》的反应是狂热的。实际上,纳沙泰尔版本(1777年)的成功让弗朗什-孔泰的书商们感到震惊,其他迹象也显示了这种对百科全书知识的狂热情绪。1772—1773年,为了争取经莫雷兹(Morez)进入弗朗什-孔泰的几板条箱的《百科全书》,萨兰的书商让弗朗索瓦·勒潘(Jean-François Lepin)不惜与海关展开了一系列周旋。他反复向他的一个朋友——皇家副代表法东(Faton)请求帮助,法东为了他多次向总督写信。他在1773年12月8日写道:“我亲爱的格里奥依(Griois),我再次向您请求一张通行证,是为了两板条箱的日内瓦版本的《百科全书》,这些书现在在莱鲁斯(Les Rousses),是属于萨兰的书商勒潘的。被禁的书只有伊韦尔东(Yverdon)的版本……我请求您能在明天给海关那边发一份许可,因为勒潘目前实在是太焦虑了。”另外,《弗朗什-孔泰公告》曾刊登过十则广告,出售《百科全书》的单行本,这说明就这部作品而言,存在着一个非常活跃的二手书市场。
穿袍贵族们(noblesse de la robe)紧跟时代潮流。韦泽(Vezet)的镇长尽管对新观念还保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但还是埋头阅读哲学书。伏尔泰当时居住在附近的费尔内,但在弗朗什-孔泰也是相当闻名,他的著作尤其在法律界被广泛阅读。但是卢梭的影响更大。弗朗索瓦·费迪南·约瑟夫·布勒内(François Ferdinand Joseph Brenez)是一名居住在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的律师,正好在大革命开始之前的1788年去世,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律师都有私人藏书,他的图书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汝拉(Jura)地区纳沙泰尔四开本《百科全书》订购者之一,而且除了36卷的《百科全书》,他还藏有卢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所有著作,以及雷纳尔神父的《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和布丰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他还有狄德罗和爱尔维修的著作。他收藏的虚构类作品有《巴黎画卷》(Tableau de Paris)和塞巴斯蒂安·梅西耶(Sébastian Mercier)的《2440年》。总之,他收藏了超过1000册的图书。布勒内出身于一个公证员家庭,与当地较低等级的贵族有一定联系;他也是火枪队队员和所在市镇的共济会团体的会员。
除了有名的启蒙思想著作,文化精英也会购买其他各种作品。最近一项关于贝桑松法律界的研究发现,“图书室中,宗教书籍的所占比例在下降” 。图书室的书架上摆放着科学和艺术类图书,还有一些地方史的书——出于对当地的自豪感——和许多小说。精英们对虚构类图书特别热衷,当地贵族中有人还订购了《世界传奇故事丛书》(La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romans)。
《弗朗什-孔泰公告》透露了当时的阅读品味,而贝桑松书商的广告则显示了这种品味的发展方向。在377本做过广告的著作中(从1766年到1773年),有8.4%是神学,7.6%是法学,21.4%是历史,28.6%是纯文学,还有33.6%是艺术和科学。从中可以看到贝桑松的书商们在形成弗朗什-孔泰的阅读习惯中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随着这种阅读行为和小团体中的图书交换,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开始发展起来。贝桑松、圣克劳德(Saint-Claude)和费索尔(Vesoul)这三个城市有了公共图书馆。读者俱乐部和社团也出现了。1771年,在圣阿穆尔(Saint-Amour)这个小镇上,“几名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向当局请求允许他们“租借一间房舍,供他们聚会、读报、玩博彩等,就像是省内其他市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的那种一样”。在贝桑松,书商皮埃尔-艾蒂安·方泰(Pierre-Etienne Fantet,伏尔泰的一个朋友)和多米尼克·勒帕涅(Dominique Lepagnez)开设了阅读室。萨兰的一名教士表示曾经从一名律师那里借过几卷《百科全书》。如此,图书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图书主人这个有限的圈子。
那么在乡村,图书的传播情况如何呢?我们首先要记得,弗朗什-孔泰位于法国东北部,那一带的识字率相对比较高。村民们之所以能读书,都是因为一些神职人员的勤勉积极。反宗教改革运动为弗朗什-孔泰识字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础;神职人员在宗教图像和物件之外,采用书籍在家庭中传播天主教义,争取村民们的皈依。在传播宗教书册方面,神职人员受益于一个成熟的商业网络,这个网络由大书商、新闻散播者和流动商贩组成——流动商贩虽然自己有店铺,但还是会到山区挨户兜售小商品。
弗朗什-孔泰的神职人员在很多方面都促进了宗教出版物的传播。例如,圣克劳德的主教梅亚莱·德·法尔热(Meallet de Farges)在他的教区免费分发颂扬虔信的小册子。布普雷(Beaupré)的传教士一个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教区积极活动,与获得当局许可的书商一起去走街串户,一方面搜查坏书,另一方面分发宗教书籍。传教士自身也成了出版者,1780年7月20日,他们获得许可印制《对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Les 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u christianisme,十二开本),这本书由其中一名传教士所写,当时一版印制了一万本。许多家庭都收藏宗教歌曲的合集,不仅在教堂做礼拜时用,也可以在家时阅读。一本题为《心灵引导法》(Méthode pour la direction des âmes,1782—1783年)的神职人员手册就清楚地解释了基督教家庭收藏虔信书籍的必要性。其作者约瑟夫·波沙尔(Joseph Pochard)以前是一名神父,也是贝桑松神学院的主管,他四次都提到:“如果一名优秀的神父发现有些家庭连十字架、宗教图像或祷告书都没有的话,一定会感到痛心不已。”他还建议夜晚围炉而坐的时候,最后可以读一读引人深思的书籍,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推荐了一些适合的图书,其中就包括以上提到的《对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以及《深思》(Pensez-y bien)、《奉献人生之入门书》(L’Introduction à la vie dévote)和《基督教教育家》(Le pédagogue chrétien)。
这些活动对于民众来说到底有什么效果呢?调查发现,只有6%的农村人口(农民、日薪工人、葡萄栽种农)藏书,其中80%都是宗教书籍。因此,宗教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流行的故事书和年历。
大革命之前几年,图书在弗朗什-孔泰的各个阶层都广泛传播。图书的种类有很大不同,而传播的原因也有很大不同。有时候,是智识上的好奇心和现代性口味决定了阅读习惯;而有时候正如我们所发现的,是宗教的宣传起了作用。最后传播到农民手中的书籍跟启蒙思想的作品又完全不同,而且事实上,启蒙思想的著作在大型的精英图书室也不见得一定就有。不过,在弗朗什-孔泰,宣传虔信的图书大量出现,这说明农村人口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真正具备阅读能力的。农民们很可能蓄势待发,等到1789年之后,时机到来,就可以顺利过渡到对世俗文学的阅读了。
政治出版物的大量增长
大革命给弗朗什-孔泰带来了印刷品传播的新阶段。有力刺激印刷的两大动力是宣传和改变信仰的需要,这两种需要主要来自两大对立派系:一个是想要击退“狂热盲信”的爱国激进分子,另一个则是绝不会被动挨打的反抗大革命者。在这场浩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双方的武器都是印刷品。传播印刷品的网络也有两个,一个使用的是革命当局的官方渠道,另一个采用的则是地下路线。目标都是要控制农村。为了这个目标,双方都到处散发小册子、小书、招贴报和报纸等,而这些印刷品都直接触及当下发生的各类事件。
我们是否能具体调查印刷材料的增长程度呢?关于这段时期印刷品的完整清单还没有编辑完成,但是已经根据印刷商和出版日期进行了分类整理。这些资料让我们对印刷坊的情况有所了解。1789年1月至5月,为三级会议而开始的选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于是在弗朗什-孔泰出现了220种题目的印刷品(包括小书和小册子)。平均每个题目的印刷品都印制了1000份,所以出版总量达到22万。几个月之后,有关《神职人员民事宪章》(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的辩论又催生了30种小册子。所有印刷坊都忙碌不停,另外在阿布瓦(Arbois)、波利尼(Poligny)和圣克劳德还出现了新的印刷坊。
将法国划分为“省(departments)”的行政划分政策将原来的弗朗什-孔泰分成了几个省,但还是有利于这种新的政府单位里的官方印刷商。在贝桑松,自1784年以来就从事印刷业的安托万约瑟夫· 西马尔(Antoine-Joseph Simard)从省当局获得了大量印刷费,但他没办法接下所有订单,所以省当局不得不再找其他印刷商(雅克弗朗索瓦·库什[Jacques-François Couché]和让弗朗索瓦·达克兰[Jean-François Daclin])。从1790年11月到1794年夏季,杜布(Doubs)省共花费5万法郎来支付各种印刷账单。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汝拉的首府隆勒索涅,在这里,德洛姆(Delhommes)的小印刷坊自1762 年以来就勉强支撑,但现在的印刷产量却增长了。自1790年到1797年期间,我们发现了20种不同的出版物,其中一篇于1794年11月30日在至高圣殿(Temple of the Supreme Being)发表的有关“诚信(La Bonne Foi)”的演讲稿一次就印刷了3000份。除了这些,还有5卷12开本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律公报》(Bulletin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革命历共和三年到四年[1794—1796])和多卷4开本的《法兰西法律》(Lois française),每卷售价4法郎,这几套书的订单都是该省在1791年11月下的,并由不同区送达每个市政府。而且,所有新法律都要印制到招贴报上。1790年,汝拉省的印刷支出达到3万法郎,占总预算的10%。还有一个例子,革命历共和三年(1794),刚在波利尼落脚的雅克维克托·贝通(Jacques-Victor Beyton)从阿布瓦区收到2500法郎的款项,用于支付大约30种出版物(包括12张招贴报)的印制费,所有出版物的印数在40到650不等。1794—1795年,他还印制了《汝拉省歌曲年历》(Almanach chantant du département du Jura)。
所有印刷坊的产出量都在增长,以满足市政、省政、区政和政治俱乐部的需求,这些机构都在通过印刷品来传播革命观念。而且,意识形态的交锋升温很快,各方都通过出版物进行反击。在反对革命当局出版的大量材料的斗争中,反抗文学也发展了起来。1791年6月1日,汝拉省政府得知,“第三和第四次印刷的教皇训谕”在流通,于是决定要印制2000份宪章主教在就职仪式上的演说稿,并“分发到每个市政厅、每个神父或教区教堂主神父手上,推荐他们在第一个星期日的圣会上宣读”;如果神父不宣读,那么政府将派该市的检查员在弥撒之后进行公开朗读。政府还建议每个公民“告发所有兜售、散发或组织散发煽动性和诽谤性材料的人”。其实在1790年的秋天,对新宪法满怀敌意的出版物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宗教形势也助长了对大革命的反抗。拒绝宣誓效忠新宪法的教士们和支持他们的网络印制了大量小册子。拒绝效忠的教士们,不管是隐藏着的还是已经被流放的,都是抵抗力量的核心;大约有2000名神父穿过了瑞士的边境。那些躲在附近或偏僻地区的教士们虽然处于一个全新的形势之下,但仍然坚持跟过去一样写作。他们的许多作品在瑞士印制,然后偷运到法国。1792年4月27日,在蓬塔利耶附近,“一个看上去像教士的外国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被捕了”。这名神父的身份很快就被揭晓,名叫让·皮埃尔·埃梅里(Jean Pierre Emery),是在汝拉附近的布雷斯(Bresse)地区的前克洛纳(Colonne)教区神父。他随身携带着一份待印刷的手稿,标题是“人们的信仰或节选自《对宗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e la religion)的原则”。埃梅里只是因此被捕的众多人之一。
拒绝效忠的神父们自身也是宣传者和传播者。在蓬塔利耶区的布耶容(Boujeon)镇,两名神父的行为就“搅乱了这里的平静,他们到处散发充斥着狂热和煽动性格言的书籍”。他们散发的还有一本标准的反宪章图书《一名汝拉省神甫的最后讲道》(Le Dernier Prône d’un curé du Jura)。以这些神父为中心,很快就成功组织了支持性网络,其中妇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皮埃尔方丹镇(Pierrefontaine,属杜布省),一个洗衣妇就“阅读各种不好的书籍,而且与她能接触到的每个人分享之”。在古镇(Goux,属杜布省),一名教师组织妇女集会,并“从一个村庄流窜到另一个村庄,通过书面文字”煽动“狂热盲信情绪”。拒绝效忠的神父们的母亲和姐妹们自然都是激进分子。人们肯定还记得,在大革命之前的20年里,神职人员就不断从农村人口中招募年轻神父,因此在农村的妇女群体中自然就获得了同盟军。1793年5月,在格拉斯镇(Gras,属杜布省),一名拒绝效忠的神父的两个姐妹被指控到处散发小书和简报。
革命当局为了反击散发“狂热”小册子的做法,就印制了更多各种各样的材料,包括招贴报、演说稿、小书和论辩的报告等。只要有人在某省或某区或者某个政治俱乐部,发表了爱国演说,当局就命令印刷这篇演说稿。印刷品的重要性被理想化,其有效性从未被质疑。地方上的印刷商印制立法文本,还有公共安全委员会会议的议程摘要等,这些与巴黎的任何一项决定都紧密相关。这些官方文件由各区转发给市镇,市镇同时还会收到同样数量的记录各省和各地方决议的材料。通过研究这些文件的路径,我们可以具体实在地了解到革命当局的决议是如何得到贯彻的。
这些各式各样的印刷材料送到每个市镇上,以便让每个公民都了解情况——这也是为收获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奥尔南(Ornans,属杜布省)的雅各宾俱乐部出版了一篇题为《关于农村的狂热分子》(Aux Fanatiques des campagnes)的檄文,一版印刷了600份,分发到整个区(1791年)。1793年9月19日,杜布省政府投票决定,免费赠送在贝桑松印刷的雅各宾派报纸《骑哨报》(La Vedette)给该省的所有市政府和政治俱乐部。市政府官员接到指示,要“在每周日和假日的晚祷之前”公开地大声朗读,因为这份报纸“以最纯粹的形式阐述了共和主义的原则”。于是,700份报纸被分发了出去。
对于双方来讲,印刷材料都有着传教布道的价值,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被广泛宣传。有关年历的争斗就例证了双方的交锋,例如《跛足的信使》(Messagers boiteux)与在贝桑松和波利尼印制的共和派年历之间的争斗——《跛足的信使》在伯尔尼(Bern)和纳沙泰尔印刷,然后秘密运进弗朗什-孔泰,但后来被省当局追查并缴获。
两种文学,一个目的
不管是通过官方的公开朗读,还是通过夜间聚会时的秘密朗读,政治信息更多的时候都是通过朗读的方式在传播。在过去,阅读是一种集体的公共行为,在178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也是村庄中的一种共同行为。教区神父高高站在讲台上,向聚集在下面的信徒们朗读法令和条例。每年在村集会上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行政官员们都要公开朗读总督颁布的公文,他们就是在总督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法规和信息就这样传递到普通民众。在弗朗什-孔泰的村庄里,民主是非常活跃、有生气的。公共阅读也发生在夜间的聚会上。在农民社会中,图书及其他印刷品就是这样被使用的,因为在农民社会,很大一部分仍旧保留着
口头文化。这种传统形式中出现的新变化就是对大革命所带来的变局所做出的调整。
众多文献都表明,在秘密的宗教礼拜上,人们会采用公共阅读的形式。似乎大多数秘密传播者也都有责任朗读他们所传播的材料,因此他们实际上也就成了口头中间人。所谓的煽动者就是因为向人们朗读并分发了书籍而遭逮捕的。反革命运动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要依靠集体性阅读。1792年8月27日,在蓬塔利耶,区总议会收到情报,说是反革命报纸,尤其是《伯尔尼公报》(Gazette de Berne)在民众中流传。《公报》会先送到郊区的一个秘密地点,之后有人会去取,然后反革命分子们就“聚在室内……向反对宪法的人朗读报纸内容”。在短时期内,这些印刷品替代了主持秘密宗教礼拜活动的流放神父。
爱国者也一直在使用公共阅读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这是一种必需。在整个弗朗什-孔泰,报纸、演说稿,甚至来往的信件都会在政治俱乐部里被大声朗读出来。有时,这种朗读带有教育目的。1792 年6月17日,在隆勒索涅,宪法之友社(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共604名会员)决定:“在每周日和所有假日,要定期在会议大厅公开朗读最好的报纸和书籍,朗读者要向受教不足的公民解释那些较难理解的内容。”省和区的革命当局都要求市镇官员向“为此目的而聚集的公民们”朗读他们所颁布的立法文本、法令和决议。
爱国神父也被召集起来参加公共阅读活动。有时候还会击鼓召集村民们来参加活动。1790年12月16日,阿布瓦区的官员们注意到,他们那个省的所有教区都收到了一篇赞同《神职人员民事宪章》的文章,并向民众展示了这篇文章,对此他们很满意。“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这次展示很完美,离设定的目标已经相当近了。”然而,这种公共阅读并不总是如此成功的。例如,茹涅(属杜布省)的国家特务就很遗憾地注意到“参加在理性殿(Temple of Reason)举行的法律发行和朗读活动的公民非常少”。
最后,汝拉省的护林官,布列塔尼的勒坎尼奥(J.-M. Lequinio)在《风景如画的旅行》(Voyage pittoresque,1801年)中所记录的见闻也是一份证明材料。他注意到上汝拉的市长在公共广场上大声朗读报纸。
他还写道,在格朗沃的圣洛朗(Saint-Laurent en Grandvaux),居民们“在读、写和计算方面都很不错,他们的一大爱好就是阅读他们焦急等待的报纸,你会发现,他们并不缺乏这些报纸能够提供的政治方面的知识”。
而且,在弗朗什-孔泰这样一个仍旧在许多方面保留了口头传统的社会里,很自然,歌曲也被广泛运用于观念的宣传上。印制的歌单广泛流传。在杜布省,一名拒绝效忠之教士的兄弟,让· 布吕雄(Jean Bruchon)因为宗教迷信扰乱治安,遭到逮捕,他到处散发的就是“恶俗的诽谤性小册子,有些还是以歌曲的形式来写的”(1793年)。1794—1795年在波利尼印制的《汝拉省歌曲年历》就是一本歌曲集,既有共和主义的歌曲,也有贵族的歌曲。在贝桑松,在弗夫· 沙尔梅(Veuve Charmet)的印刷坊还发现了一首题为《哀悼路易十六》(“Lament on the death of Louis XVI”)的歌曲(1796年3月)。1795年4月,一名边境卫兵报告说,他在翻越高山时,听到“有三个男人在高唱一首贵族的歌曲”。不管是印制的还是口头传播的,歌曲都是快速传递意识形态的通讯员。
革命时代,两种对立的政治运动明显加速了印刷材料对弗朗什-孔泰整个社会的渗透,尤其是对农村的渗透。在传统的,主要是宗教性质的文学作品之上,叠加了一种新的、与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文学形式。在农村,首次出现了政府公报和报纸。然而,虽然印刷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而且流通量也增长了,但是阅读的方式却没有发生改变。在这个仍旧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政治信息,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是通过朗读的方式在传播。

《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美]罗伯特·达恩顿、[法]丹尼尔·罗什编,汪珍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11月。
上一篇: 首届绿色数字印刷产业发展论坛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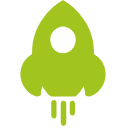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